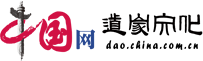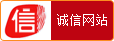道入乎藝 畫載乎道
——道士畫家黃公望

黃公望,是著名的畫家。在元代畫壇上,山水畫成就極豐富,藝術品格也高,且對后世影響巨大。而黃公望正是領軍人物。畫史上稱元代成就高者有四家,公望為其首,而與其他三位關系密切。如果談到傳世名畫,《富春山居圖》自然不能不提,其作者,正是黃公望。但常見說此畫者大半不提起黃公望的道士身份。只在專業圈子里或有人提起,但多數人仍知之不詳,更少有人指出,作為畫家的黃公望,和道士黃公望,是人格統一的同一人,而且深一步看,其畫作的品格,與道士的品格,原本互相滲透,互相成就。他是善畫的道士,又是把道教的精神貫穿于繪畫的大家。
本文想將道士與畫家,看成黃公望的同一人格,畫的逸品很大程度上全真道士的飄逸同構。

一、一代高道
據一些材料記載,公望本姓陸,為三國吳丞相陸遜之弟陸瑁的后代,世居松江,其父遷居江蘇常熟,他出生于常熟。“少喪父母,貧無聊賴。永嘉黃老年九十無子,乞為嗣。曰:黃公望子久矣!因名而字之”。黃氏雖說永嘉人,那應是就籍貫言,其時正寓居常熟。清同治《蘇州府志》九十八稱:“永嘉黃氏老無子,居邑之小山,公望姿秀異,愛之,乞以為嗣,公望依焉,因用其姓。”
黃公望也有過出仕的經歷。小時應神童年科,好象沒有什么結果。一度賣卜為生。后有兩次為吏,本來是通往做官的狹徑,最后卻成了他人生的大噩夢,而且也成了他入道的大背景。第一次,是得到浙西廉史徐琰的賞識,做了浙西憲吏。但是一天,突然穿上黃冠服,引來一片奇怪的眼光。不知道他這樣做是道門宿根,還是通過與官場的接觸看到了某些黑暗的內幕,反正是第一次作吏就以穿上黃冠服告終。第二次在元大都,做了察院掾。王逢《題黃大癡山水》有小注:“嘗掾中臺察院,會張閭平章被誣,累之,得不死。遂入道云。”對于張閭,當時人評很差,說他是一個貪官。延佑二年(1315)九月張閭遭逮捕下獄,黃公望也無辜受牽連入獄。那年黃公望46歲。經六七年,出獄后便隱居不仕,歸常熟,并加入全真教,自號“大癡道人”、“一峰道人”。常來往于常熟、松江、富陽、杭州一帶,講道賣卜,邀游山水。算起來,他入全真教時,已經五十四、五歲。
黃公望的入道,遭際大禍是一個大背景,蓋由此徹底砍斷了他走仕宦之途的希望,更看清了社會的黑暗和前程的無望,終于在全真道中找到了人生的價值。同時,也不能不提起他的師父金蓬頭。
黃公望之師金蓬頭,是當時著名的內丹家、全真道士。對此人的研究目前還不夠。各種書都說金蓬頭為全真道士,他的師父為李月溪。但對李月溪的師承,說法不同。據文獻,李的師承,有兩說。一據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續編》卷五《金蓬頭》,李溪月為“真常李真人之徒。真常,長春丘真人之高弟也”。是李溪月為丘長春再傳。而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峴泉集》卷四《金野庵傳》則稱說野庵“師全真李月溪。月溪,白紫清之徒也。”如此,則金蓬頭初事的乃是南宗門人。按他曾居武夷、龍虎二山,張宇初作為天師,本居龍虎山,對于龍虎山的典故應當很熟,說的當較為可靠。據張氏載,李月溪一見器之,“命游燕趙齊楚求正焉。及參先德李真常,益有省”。《歷世真仙體道通鑒》所說也同。故金蓬頭見李真常是游燕趙齊楚之遇,可能人們將此事與李月溪的師承混了。愚意,金為白玉蟾一系人的說法當可信,證之他的行事,也有跡可尋。張宇初說,“時四方聞其道者無遠近,有患疾輒叩之,以所供果服之,無不驗。由是信者日集。嘗天旱,叩龍井召龍出,語龍出聽,逾時漸小,躍入袖中,乃警以偈,龍感奮入水。未傾,天雨。”這是典型的南宗作派。自白玉蟾之師陳楠起,兼行雷法。特別是白玉蟾,受上清箓,肘后常佩大雷隱書,為雷法名家。而自王重陽起,人稱不事神奇,雖然重陽子實際參與過多種科儀,且篆符上表,后來七子以下,參與醮儀也屬尋常,且后世的記載中也有些神奇的故事,但畢竟還保持重陽宗風。而雷法中素有驅龍卷水一類法術,所記召龍出聽云云,不過是對此的模寫,卻更雖加上了活龍出現之類細節。金后來隱居武夷山止止庵,或也有歸宗之意吧。
正德《松江府志》:
黃公望,字子久,號一峰,又號大癡。……補浙江省掾,忤權豪,棄去,黃冠野服,往來來三吳間,開三教堂于蘇之文德橋,至松寓柳家巷。后隱杭之筲箕泉,已而歸富春,年八十六而終。
由此可見,他入道后,往來三吳,在蘇州曾進行全真道的弘教活動。全真道重要的特征,是提倡三教合一。當年王重陽組織大家入道,曾開幾個以“三教”為名的“會”,如三教平等會、三教金蓮會等。黃公望對三教平等、三教合一等觀念也深信不疑。其《題馬待詔三教圖卷》稱:“昔在姬周時,養得三個兒。不論上中下,各各弄兒嬉。胡為后世人,彼此互瑕疵。猶如龍舌頭,三岐而一岐。我不分彼我,只作如是辭。”三教堂正是宣揚推行三教平等思想的一個陣地,據說當時僧人道士來學的甚多。不過他更多時間是住在松江杭州富春一帶,晚年最后定居于富春,而常出云游。《自題富春山居圖》說,無用師約他畫山居圖,但數年未定稿,就是因雖居山中,常出外云游之故。
明《道藏》中收有黃公望傳的的著作三種,都是講內丹修煉的。三書都題“嗣全真正宗金月巖編,嗣全真大癡黃公望傳”。所以這三種書,都是金月巖編,公望只是傳者。同時這一排名方式,也說明黃公望恪守其師之說,三書也代表了他們共同的觀點。三書為《紙舟先生全真直指》、《抱一函三秘訣》、《抱一子三峰老人丹訣》此金月巖為誰?在金蓬頭的現有資料中,皆沒有提到他有“月巖”的號或字。此點使人不能明。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指出:“金月巖未詳,或疑即金志揚(野庵)。”愚意,月巖當即金蓬頭。黃公望《金蓬頭先生像贊》:“師之道大,此特其跡。普愿學者,惟師是式。大癡道仆黃公望稽首拜贊。”佩服之至,既“惟師是式”,則不會再有其他師傳。且當時也沒有其他足以使他折服的道者,各類仙傳和全真道教資料也沒有提到黃公望另拜其他人為師。
黃公望承其師說,以全真“正宗”自居。他們所說的全真,從組織說,從五祖七真開始,而從學理上說:“夫全真之學,直究玄宗,乃單明向上大道,非小乘眾學雜術之比。自五祖七真出,而天下得道者皆直指自證,以心印心,不立片文只字,其妙在此。后世有學者眾,其所師得人,則其說皆合符節。所師非人,或受頑坐枯心,或吞精咽氣,或存心想賢,或雜傍門,非獨無益,而又害之。且全真把柄于父母未生前,真已全矣。生亦不增,死亦不減。若人以心印空,覺悟本真,則真自全,金丹之道具,而大藥之基立矣。”他從性本自己固有的觀念出發,指斥“或謂金丹乃神仙之道,必有口受師傳密語,或指大道,謂之單修性宗,不達命宗,不得成仙道”的觀念。從這些議論看,金蓬頭雖由南宗入北宗,但卻頗體現了強調“性”的傾向。而認為:“若能悟全真之妙,念念相續,專炁致柔,照一靈而不昧,返六用以無衣【翳】,守一忘一,至虛而靜極,靜極則性停,性停則命住,命住則丹成,丹成則神變無方矣。”“性停則命住,命住則丹成”,特別明顯呈現出北宗先性后命的特征。
他反對各種“傍門小法”,以為不關修性之事,“爭知性命二字,尚有真假。真性者,出陽神也。陽神者,此是天仙大成之法也。假性者,出陰神也。此是仙鬼小成之法也。可笑此等出陰神之人,奈何少學無知之徒,不達抽鉛添汞煉金丹大藥之術,又豈知伏龍降虎之法也。卻妄內觀,存想下丹田,安心定意,固養神炁。言我決成功。意內成金丹,想中取大藥。此等有如小兒戲耍也。”他并不是一概徹底否定存守丹田等法,而認為只是初修之士入道的法門。而出陽神與出陰神的區別,乃是南宗的老話頭。在張伯端的故事中,就提到過。《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卷四九《張用成》說,張紫陽與一位禪師約定,出神至揚州看瓊花,各折一枝回來,但醒來之后,張紫陽手里拿出一枝花,而禪師卻一無所有。后來門人問起緣由,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聚則成形,散則為氣,所至之地,真神見現,謂之陽神。彼之所修,欲速見功,不復修命,直修性宗,故所見之地,人見無復形影,謂之陰神。”可見黃公望雖然認為“性住命住”,將修性放在第一位,但性命雙修的基本立場仍然不變。所以三書中講到具體修法節次的時候,還是體現了性命雙修的基本樣貌。
他自稱得“七真形神俱妙七返合同印子”對金丹的基本節目作了介紹。認為其大關要,乃在明金丹之祖,造化之宗。在此基礎上,以形神關系下手討論。稱:形神相證,實悟至真;形神相顧,入道初真;形神相伴,名曰得真;形神相入,名曰守真;形神相抱,名曰全真;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形神雙捨,名曰證真;普度后學,以真覺真。此處說的“合同印子”,他處文獻未見,不知是否當年李真常真的是有所傳,還是他們的自悟,且不來詳考。只說他們用形神關系作內丹的基本理論,在同類著作中很有特色。
按形神觀是道教重要的理論領域和修行指導,還曾經與佛教展開過大論戰。陶宏景和他的法裔們都參加了論戰。但從唐吳筠《神仙可學論》、《形神可固論》之后,極少有人從形神關系發表正面論文。其實,修煉金丹,根本的還是要解決形神永固的的問題。只是隨著宗教實踐的深入,內丹家深入到人的生命的本源,“大藥三品,神與炁精”雖是后出的理論,卻是長期探索的總結,早已是內丹理論的基礎。這三品的觀念,看似不直接談形神,實是形神觀的深入。此且不去深入。總的一句話,沿著形神觀的理路去討論內丹學,是金月巖、黃公望的一大貢獻,也是一大特色。
傳出三書,是黃公望承其師做出的重要貢獻,也是他丹法思想的基本面貌。三書的研究還有許多內容,限于篇幅,且暫打住。
二、畫壇領軍
黃公望以畫著名。在當時的畫壇上,有很大的號召力。他的善畫,當然靠其自身體悟和精進努力,但也有各種因緣成就,曾經得趙孟頫指點,就是他繪畫的極大幫助。
趙孟頫在元代畫壇、文壇上、書壇上,都是一個引領風騷的人物。公望能在在畫壇上獨放異彩,與早年得趙指點是分不開的。《題趙孟頫書千文》:“精進仁皇全五體,千文篆隸草真行。當年親見公揮灑,松雪齋中小學生。”這是他七十九歲時所題,“小學生”當指其年輕時,也可指在公雪面前自己還是個蒙董孩子,謙遜和記實兼而有之。其《自題畫夏山圖》:“北苑夏山圖,曩在文敏公所,時時見之,入目著心。后為好事者取去不可復見。然而極力追憶,至形夢寐。今歸之叔明,獲在收藏之列。但可觀其意思,而想象其根源耳。然而今老甚,目力錯花,又不復能作矣。時至正壬午大癡道人書。”這也是他晚年所題,實際有一段學藝的回憶。公望論畫,極力崇董源,稱“作山水者,必以董為師法,如吟詩之學杜也。”他的服事趙孟頫不知具體的細節,特別是一個平民小子如何進入趙府門墻,得到趙什么指點,也不清楚。但趙為當時畫壇領袖,處于他身側,耳濡目染,獲益或在不經意間。松雪本來有意摒棄南宋院畫積習,推崇董源的畫風,而作為宋宗室又仕于元,既富于藏,又精于評,對他的觀摩是一種指點,而他則由此可以深刻體驗。“入目著心”、“極力追憶,至形夢寐”這幾句真是入木三分。同時,在趙身邊,能見他作畫,簡直就是親受教導了。《趙文敏〈草木幽禽圖〉》:“嘗記松雪翁為王元章作《幽禽竹石》,甚為合作。屈指三十年,今復見之,恍如夢覺。上有山邨題詠,尤是佳句,使人三嘆。至正五年十月望日大癡道人題。”至正五年,為1345年,公望七十六歲,推前三十年,是1315年,正好是他被累入獄的那年。可能他直到被捕前都還與松雪來往。如此,這一“小學生”,實受松雪指點直到中年。由此記述,可見他有機會觀摩松雪作畫,則得益多多,毋須懷疑。
又有一些材料,說金蓬頭善畫,是否對黃公望也有影響待考。當時畫壇上流派不一,金蓬頭的另一位弟子方從義也是著名的畫家,黃方二人也有交往,但方與黃的畫風不同。陳傳席《中國山水畫史》將黃公望看成“元畫變法的成熟者”,而將方從義看成是“元畫放逸的最高峰”方從義與黃公望同師金蓬頭,畫風則相差甚大。所以即使金真善畫,對黃公望的直接影響也不甚深。
歷來論其畫,都說他師承五代董源、巨然,后再變其法。正德《松江府志》稱:“公望善畫山水,初師董源巨然,后稍變其法,自成一家,所著《寫山水法》,至今多宗之。”如此,松雪可看成他學畫并形成自己風格的過渡津梁。
公望畫作甚多,也被當時人們十分看重。但說到現今人們的印象中,似乎《富春山居圖》最為深刻。除了這畫的傳奇經歷之外,其藝術上的非凡造詣更是名至實歸。公望《題自畫富春山居圖》述其緣起:“至正七年,仆歸富春山居,無用師偕往,暇日于南樓援筆寫成此卷。興之所至,不覺亹亹,布置如許,逐旋填劄,閱三四載未得完備。蓋因留山中,而云游在外故爾。今特取回行李中,早晚得暇當為著筆。無用過慮有巧取豪奪者,俾先識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難也。十年青龍在庚寅歜節前一日,大癡學人書于云間夏氏之知止堂。”無用師,名鄭樗,號散木,全真金志揚徒弟,黃公望師弟。盱江人。盱江古稱汝水,撫江的上游,流經江西省的南城、南豐、廣昌三縣。鄭樗雖說是盱江人,實居住于松江一帶。而他請黃公望題詞時,正在松江夏氏知止堂。此幅作品,經歷三四年猶未完稿,是少有的精品中的精品。甚至有人將之將之與王右軍的書法《蘭亭序》相比,認為達到圣而神的地步。此圖為長軸,縱33厘米,橫636.9厘米,畫富春江一帶山水,山峰起伏,平崗連綿,江水如鏡。“而畫上數十峰,一峰一狀,數百樹,一樹一態,天真爛漫,變化極矣。”這一畫中,也運用了各種繪畫筆法,似乎是公望一生藝術的大展示。
當時人們對黃公望十分推崇。后世將他和倪瓚、吳鎮、王蒙合稱元四家,認為他們代表了元代山水畫的最高成就,而黃在四家之中年齡最長,也有引領之氣象。著名畫史專家俞劍華先生在所著《中國繪畫史》中評論元四家時說、“四人雖亦上追董、巨,不離古人法度,然能自具面貌,取古人之神,而不泥古人之形,又能飽遨觀飫,日徜徉於名山之間,而文章道德,又皆加人一等,故其所作,自異凡響,水墨渲淡與淺絳著色一派乃底於大成,為明清數百年之宗主。蓋山水畫至元四家已至爐火純青時代,其醇厚之趣味不在表面,而在內容,令人百讀不厭,真絕詣也。”四人中尤其黃、倪更為突出。清人至謂:“元代人才,雖不若趙宋之盛,而高士特著。高士之中,首推倪、黃。”清初畫壇“多宗云林、大癡,名流蔚起。承學之士,得其一鱗片爪,亦覺書昧盎然”。《中國山水畫史》則說黃公望“繼承趙孟頫之后,徹底改變了南宋后期院畫陳陳相因的積習,開創了一代風貌。”“總之,元以后,凡有山水畫的地方,皆有子久的影響在。中國山水畫史上沒有任何一個畫家影響能超過黃子久。和子久的影響差不多的,只有一位倪云林。”
三、道畫相攝
黃公望的畫,當時人秒稱他入“逸品”或“逸格”。
中國的山水畫從南北朝開始,逐步成為獨立的畫種。唐宋時期,山水畫發展很快,出現了許多有名的畫家。到了元代山水畫不僅盛極一時,而且繪畫水平也超越前代,對以后的中國山水畫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們傳世的作品極多,向來為人珍藏。黃公望、倪瓚等之所以會有這樣巨大的影響,還不僅在畫技的高超,而在于繪畫領域中代表著元代以降的潮流,即是他們的畫作,推動了中國繪畫中“逸格”的完成。對逸格的推崇,開始是宋人黃休復在《益州名畫錄》中提出來的。他繼唐朱景玄之后,將畫分為四格:逸、神、妙、能,而以逸格為首。所謂“逸格”即是“拙規矩於方圓,鄙精研於彩繪”,“筆簡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於意表,故目之曰逸格爾。”逸的標準雖然提出於宋代,但“逸”的作品的大面積成熟,卻是在元代山水畫中,首先是元四家的作畫中,而恰恰黃公望作了四家的第一號人物,倪瓚則是四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這種情況,決非偶然。
原來逸格的特點是“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於意表”的。它比神、妙二格不同的地方在于妙格雖然“曲盡玄微”,神格雖然“思與神合”,“妙合化權”但“玄微”“化權”,都還在人的主觀精神之外,是人們的追求、再現的對象。而逸品的要義“得之自然”,“出于意表”,藝術家的精神境界不僅已經理解了造化、把握了自然,取得了審美的自由,而且根本就與“自然”“造化”溶合而一。所以它與師法造化比,在把握美的自由境界上又深了一層。這樣的一種高度的審美自由,在中世紀的特定環境中,只有佛、道二家的超塵出俗才容易做到。而在與自然的接近、對造化的追求的把握以至融匯,開始時道教徒重視一些。
要說清這一點,我們且引一段《莊子·養生主》中庖丁解牛的故事。
我在數年前,為路沛庚道長《崇道進藝錄》(為所書道經,小楷精妙)作序,就曾引此故事,以論王羲之的書法藝術:
(故事)說庖丁解牛,全沿牛之肌理而行刀,不僅游刃有余,而且其動作十分優雅,中音樂節奏,合舞蹈姿態。庖丁自己解釋達于此境的緣由:“臣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庖丁解牛,是由道進乎技,逸少之書,則是好道進乎藝。王羲之的字,是時代之美,曠代之美。而其美之源,乃在于道的滋養,故能不受古法束縛,進入創作的自由。一旦精神得到解放,其運筆構形,婉轉自由,便不同凡響,而充分表達著自己的獨特風格。
這個寓言,寫得很美,所以許多人喜歡讀它。而“好道而進乎技”的寓意則不一定每個讀者都重視。其實,對于道和技的關系,素來有人關心,只是后世的討論不太多罷了。此且不論。愚意,此處于對于對道的體悟能否進乎技術的層面,顯示了形而上與形而下能否統一,或者說個人能否在實踐中—下面討論的主要的藝術創作的實踐中—將之統一起來。從莊子這個寓言看,他是認為可以統一的。而古人的所謂“技”,是包括了藝的,即是我們今天認為是藝術的東西,古人將之和技術、技巧并列。《后漢書》的方伎列傳,《晉書》的藝術傳》,包含的都是醫、相、卜、圖,一類人。而且,庖丁在道進科技后表現出來的,正是一種如舞蹈般的優雅自如,中乎音樂之節,已經是藝術化了。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將莊子說的故事,引用來解釋道與藝的關系。黃公望的藝術成就與道教的修煉有成,正是道入乎藝的結晶。
為什么黃公望等修道、繪畫能致于化境?古來都說他的畫有仙氣,人也如神仙,那么這種仙氣是怎么與畫藝結合在一起的?竊以為有幾點是特別重要的。
一是融入自然的生活方式。道教倡導“道法自然”,自然,是沒有經過人為加工的萬物的本然,也就是它們本來的狀態,有自己變化的節奏,按其本來的面貌和變化趣勢去生化演變,便是法自然的要義。簡單地說,自然也就是自然而然。人們所能做的,只是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為,指人為,脫離了自然的主觀行為絕不能做。自然義不等同于“自然界”,但自然界還保持著未經人雕鑿的面貌,所以道士們會對之有特殊的情感和感悟。遠離塵囂(當然,這里的離,并不一定指不近人間世,而也可以是陶淵明所說的那樣“心遠地自偏”),融入自然,是他們的生活方式,所謂“逸”、“飄逸”、“逍灑”,乃至于“仙風道骨”都是對此類生活方式和風貌的形容。
道徒一一除去那些借道謀富貴者之外——的生活,正是名符其實的逸的生活。即以黃公望說,倪瓚等人早目之為“仙”。后人評論云:公望“嘗於月夜孤棹舟,出西郭門,循山而行。山盡抵湖橋,以長繩系酒瓶於船尾,返舟行至齊女墓下,牽繩取瓶,繩斷,撫掌大笑,聲振山谷,人望之以為神仙云。”所以清·姜紹書《無聲詩史》評他的畫“瀟灑絕倫,獨立霞表,其仙是也。”全真道的修行有多方要求,但以內丹為正途也是最深之途。這些人的的宗教修煉追求“與造化同途”,為他對逸的境界的把握奠定了基礎。元四家尤其是倪、黃的這種逸品的完成,對中國畫壇的審美趣昧影響是巨大而綿久的。由他們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的山水畫實在浸透了道教的精神,一如自然界的真山真水曾孕育過仙真高道一樣。
二是對畫技精益求精的求,才能道進乎技、進乎藝。說是道進乎技,旁人只當寓言讀,或作哲理想,但對于真想達到如此境界的藝術家來說,卻要經過長期的探索(開始的時候還只能說是摸索),只有兩者相互契合融入無間時,才能達到。黃公望對于畫法的重視不僅表現在他對董源等畫作的深入觀摩,以至于入目著心,形諸于夢,而且也留下了對一山水技法的著述《畫山水法》。此一文章,當時傳播頗廣。除發對古人筆法的領悟,還有對真山水的觀摩托。有人說:“余家有子久《層巖迭嶂軸》,林木蒼秀,山頭多磐石,是披麻皴而兼斧劈者,絕似虞山劍門奇景,想《浮嵐暖翠山東房圖》不是過也。”又有人說:“公望居小山,日以酒發其高曠,恒臥于石梁,面山飲畢,投罌于水而去,卒悟山水神觀。后村人發其罌,殆盈舟焉。”這兩則文字都指出黃公望對于“山水神觀”是在長期面山飫看后才有所“悟”。所以,黃公望對于繪畫的精益求精,與對大自然的他觀摩、領悟是分不開的。《寫山水訣》自是畫山水法的總結,說明對于技法的追求,鉆研;其中既有對古人筆法的承襲,更多是他在飽觀自然后的領悟,兩者的結合才使得他能別開生面,領一代之風氣。沒有這些,道進乎技,就無所依托,成了一句空話。
其三,是修道者的唯象思維與藝術創作思維的高度一致。
如果從更深的維度考量,道教與包括繪畫在內的藝術能夠相融相攝,是兩者的思維方式的類似。道教中有一種存想法,在他們的科儀、法術和修行中普遍運用。這種方法的特點,在于豐富的想象力,更是用鮮明的形象,從仙真神將的形象,到虛擬場景(如上天入地的歷程,召將驅邪的戰斗)的展示。所以道士經過存想的訓練,形象思維的能力都有很好的基礎。司馬承貞一見李白就說“子可與同游八表之極”,那游是游仙之游,但同時又是太白無窮的文學想象力的贊美。陸機《文賦》,說作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鶩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這里說的是文學創作。其思維過程,從收視反聽開始,思想集中于創作材料的搜尋,讓心自由地翱翔,那效果達到情感越來越鮮明,眼前出現了越來越清晰的形象,再加上喚起原來積累的文學才能,再遠的物事都清晰在面前,再深再細的物象都能感知。接下來,才能有創作的啟動。這類思維活動,與前面說到的“神游八表之極”有異曲同工之妙。與李白同一朝代的白居易《長恨歌》,寫到唐明皇思念楊貴妃,道士能“上窮碧落下黃泉”地尋找,結果兩處茫茫皆不見,再去蓬萊仙島找到太真。據說,當時確有明皇讓道士尋太真的本事。白氏《長恨歌》前有陳鴻寫的《長恨歌傳》,說明原有蜀中道士自稱有李少君之術即讓人見到心中思念的亡人之術。并述其尋找太真故事。元和元年冬十二月份,他與質夫會見白樂天,說到此事相與感嘆,因請白“試為歌之”,白應命,這便是《長恨歌》所狀寫的“本事”,那么那些上天入地的描寫,是白居易有關道士作法的實錄,還是自由的發揮,還真難分辨。舉的雖是文學史上的例子,實際上與一般藝術史,和藝術創作,也都相通。藝術與理論,當然可以相通,但理論思考必用邏輯思維,是抽象的,藝術則必須靠形象思維。道教徒在修丹法的過程中,始終要以形象引導體內精、炁神的運動,而沿著所謂奇經六脈運行。為了表現這種運行,丹家畫了許多圖來表示,蓋因這這種精、炁、神的運行,迄今也無法進入精確度量,只能意會不可言傳,而圖形則可以補上人腦思維方式的不足,圖是一個形象,語言論可以詮釋其理,卻無法完整地把握其整體,只有憑自己的感受、體悟。圖,不等于就是“丹”的修持、把握本身,卻是它形象的表達。因為對他的感悟,各人如飲水冷暖自知,也就是有相當的模糊性,而圖形的象征則有更多的自由體悟的余地,如果要詮釋,則有無限的可能。這些圖中最重要的有《河圖》、《洛書》和《太極圖》。這些唯象思維的方式,黃公望一定非常熟悉。在《抱一函三秘訣》中,也運用卦象、河洛圖書,對修丹中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常用術語加以詮釋。這些都說明,他運用唯象思維相當自如。我們用唯象稱從《周易》卦象為源頭的思維方式,是因為這種思維,是企圖用形象來探測、表達宇宙最深的奧秘,表達最深的真理,也就是道,或道的運行,與平常的理性思維有共同的目標,與藝術中的形象思維有所區別;但是在思維的工具來看,是象和象的聯絡、推移,這點與尋常邏輯思維運用抽象的概念大相徑庭,而與形象思維卻極為契合。道入于技,思維方式的融合是重要的條件。所以,黃公望他們,過著“逸”的生活,用自己的體驗、領悟深入到生命的最深處,也深入到自然奧秘的最深層,在”奪造化之秘“的進程中,既提升著生命本身,又體察到山水畫的精要,將自己的體悟通過”技“的過渡,對象化為筆下的山水。可以說,黃公望和倪瓚等人的畫雖然沒有神仙造象,卻浸透著道教的精神。他們是畫中的神仙,畫則是神仙理想的體現。道與畫,在他們那時是一而二,二而一,相映無痕,渾然一體。
于是,有了被視為神仙的黃公望,也有了千古稱絕的山水畫。
作者:劉仲宇(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資深道教研究專家)
相關文章